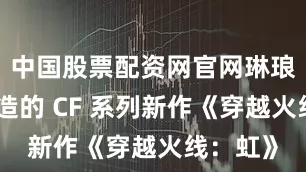1951年11月初,朝鲜清晨不到零下十五度,志愿军第七师炮兵运输分队顶着寒风向前沿递送弹药。雪随炮声抖落,地面震动让人分不清是冷颤还是战栗。颜邦翼弯腰穿行在仅容一人通过的地道,背后的木箱里装着炮兵急缺的加农弹,每一步都像踩在鼓点上,急促又不能出错。

地道拐角处,一名军官迎面而来。军官身形瘦削却挺拔,咳嗽声短促而压抑,脚步依旧稳健。二人擦肩的瞬间,颜邦翼险些失手,木箱碰到土壁发出闷响。他停住,呼吸不稳,目光死死锁住那背影。战友低声催促,他却喃喃一句:“那位首长,像极了父亲。”声音细得像埋进雪里的火星,却点燃了旁人好奇。
运完这一趟弹后,部队短暂休整。颜邦翼掏出一张几乎看不清轮廓的老照片,指尖蹭掉一层泥,却蹭不掉岁月的折痕。照片上那个青年留着寸头,眉骨高耸,正是母亲口中“抗战时已牺牲”的颜伏。照片旁有一句用铅笔写的小字:“家国为大,勿念。”十多年过去,字迹早被抹去半边,但那份重量从未消失。
同伴接过照片,皱眉思索:“这不就是咱师长吗?师里姓颜的不多。”一句话,石子落水,水花炸开。颜邦翼胸腔仿佛被炮火轰击,震得耳膜嗡嗡,却不敢冲动。他清楚,战场上一颗私心可能换来连队伤亡,父子再大,也大不过任务。于是他把照片收好,随手抓起铁锹去巩固阵地,用力之大,木柄渗出血痕。

颜邦翼为何一直以为父亲牺牲?这得追到1932年。那年他两岁,父亲颜伏在北平加入地下党,负责转运情报。为保护家人,他故意放出自己已遭捕身亡的假消息,与家彻底失联。母亲带着孩子颠沛在战火中,用纳鞋底、卖首饰换来三餐,也用那张照片撑起孩子对父亲的全部想象。
另一边,颜伏在敌后游走,先是在苏中组织青年抗日,再随新四军转战淮海。泰兴城夜袭,他左手中弹仍握信号枪;彭庄阻击,他顶着高烧策应三昼夜。肺结核伴随伤口化脓,几次高烧到神志模糊都没离开指挥所。抗战、解放、再到1950年入朝,他从宣传骨干成长为第七师师长,但他缺席了儿子成长的每一天。
1951年11月的那次擦肩只是序曲。翌日清晨,第七师炮兵阵地遭敌炮火覆盖,指挥部急需弹药补充。颜邦翼主动担任前突斥候,领着三人小组探清塌方地道,为运弹开路。泥土还在滴水,他就趴在碎石中挖通十几米狭缝。碎石划破面颊,他不叫疼,心里念的只有一句:师长必须拿到炮弹。
傍晚时分,补给顺利抵达,敌排炮被压制。师部传来口令,运输分队全部归位休整。颜邦翼在防炮洞口站了整整十分钟,终于鼓起勇气请求警卫员通报。深夜营帐内,油灯很暗,颜伏伏案整理战损统计,咳得纸张微颤。门帘掀起,两人隔着灯焰对视,彼此怔住,却瞬间读懂了岁月留下的痕迹。
“报告首长,颜邦翼,请求发言。” 军官放下钢笔,声音沙哑:“讲。” “可能…是家事。”字未完,人已哽咽。

对话不过两句,却结束了十九年的漂泊。颜伏起身,咳嗽连连仍伸手握住儿子的肩,指尖在颤。半分钟后,他说出三个字:“辛苦了。”没有煽情,却掷地有声;没有父与子的絮语,却包含战士对战士的敬意。
按规定,战场上禁止私自认亲影响军心,父子约定保密至回国前。此后数月,颜邦翼依旧运弹、救护、排险,他的勤勉被连队私下称作“老颜那股子狠劲”。师长在作战会议偶尔把目光投向运输表,看到儿子名字时,会用咳嗽掩饰情绪。两人彼此督促,又彼此守望。

1953年,停战协定签字,大部队撤回鸭绿江。丹东火车站简易站台上,颜伏终于能够公开握住儿子的手。同行官兵抬头看蓝天,没人取笑那对眼眶发红的父子,因为每个人都在擦汗,也可能是在抹眼泪。回国授衔时,颜伏被授予大校军衔,后晋升少将;颜邦翼凭三等功留队,从排长做起,没有任何跨级提拔。
难得的是,父子俩在同一座军营共事三年,从未让亲情左右决策。颜邦翼因训练事故担责写检查,父亲在会上点名批评,语调冷到让人起鸡皮疙瘩。会下,师长独自坐在办公室咳嗽到深夜,队医劝休都被拒绝。按照老兵的说法,他既是严父,也是在替当年缺席的十九年补课。
1960年代初,颜伏病情恶化退出现役,在总政编史室整理抗战资料。生命最后一年,他常翻那张旧照片,新添一行字:“一生两件事:打胜仗,教好儿。”字迹歪斜,却力透纸背。告别仪式上,颜邦翼没有穿便装,而是着新式军装站在棺前,敬完标准军礼,才让泪水滑落。他说,“父亲兑现了承诺,我也没有愧对他的信仰。”

回头看,这段父子重逢故事之所以动人,并非戏剧性的巧合,而是两个时代选择的必然——一个为了理想割舍亲情,一个为了信仰奔赴战场。正是这份“先国而后家”的坚守,让他们在炮火里重新相认,又在和平中继续并肩。对今天的人来说,硝烟已散,但那份肩上的担当、不计私利的原则,仍是值得细细品读的沉甸甸的遗产。
2
理财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360配资还涂着鲜艳的粉色指甲油
- 下一篇:2020炒股配资苏亚雷斯推射被挡错失良机